「老師,你願意相信我嗎?」這孩子回頭看了我,問道。我永遠不會忘記那雙恐懼又無助的雙眼。
她是一個長期遭受身體與精神虐待的孩子。事情發生在幾年前,基於助人倫理及保護當事人,我對這個故事的內容做了「許多」改編。
—
有一天,幾位同學鬼鬼祟祟地來到我面前,問我有沒有空聊一下。他們告訴我,班上有個女同學在家裡被母親毆打得很嚴重。
「老師,是她親口告我們的,我們還看到胸口的傷疤,很噁心!」同學們你一言、我一語地說。
「為什麼她會告訴你們?」我問道。他們說:「她來學校臉很臭,我們問她怎麼了,她就開始哭,後來全都跟我們說了。」
「對了!她還說,不可以告訴學校老師!」同學們用嚴肅的口吻說著:「她說,如果被老師知道,回去會被打更慘。國中時就曾經這樣過了……」
我的眉頭一皺,發現案情並不單純……
—
謝謝這些如天使般的孩子們,即使被託付要保守秘密,仍然知道事情的嚴重性,前來告訴我,顯然希望我可以幫幫她。我琢磨著該怎麼做才好,事不宜遲,立刻把她找過來。
「老師,沒有啦!我是跟他們開玩笑的。真的沒有這件事情!」
儘管我的態度和善,這孩子仍然矢口否認。這很正常,保險起見,我仍通報了社會處,請社工來一趟,看看她的傷口。她說胸口的傷是自己不小心撞到的。
社工家訪後,告訴我,孩子與父母口徑一致,都說沒發生這件事。就這樣,本案不了了之。
—
過了半年,這班導師來找我,從班上同學那裡得知,班上某同學在家被打得恨慘。又是她!我再度把她找來。這孩子戴著口罩,顯然臉上有傷。
又像上次一樣,她堅稱沒事,臉上的傷是自己跌倒擦傷的。啟動社政系統介入,社工幾次家訪後,也沒能找到著力點。這件事又在此作罷。
然而,這孩子不願意再來輔導室了。於是,我寫了封信給她:
我知道,一定曾經發生過什麼事,妳也很希望有人可以幫助妳。只是妳感到擔心、害怕,這我可以理解。不過,在這個節骨眼上,只有妳可以幫助妳自己。只有妳願意,才有可能獲得幫助。請妳好好想一想,需要我協助時,我隨時在這兒等著。
半年後,就在我幾乎快要淡忘這件事時,這孩子突然出現了,她是自己踏進門的。我正納悶著,她說:「老師,可以跟妳談一下嗎?」
—
「我媽媽精神不正常,平時管我非常嚴,晚幾分鐘到家,就會被她毒打。有幾次很誇張,把我的頭抓去撞牆,還曾經拿高跟鞋的鞋跟猛踹我的胸口。我媽說,她在縣政府都有認識的人,誰去通報都沒有用……」孩子邊哭邊發抖,但仍強忍著情緒把話清楚地說出來。
「所以,前兩次同學所說的,是真實發生過的囉?」我想確認。「對!是真的。對不起,我沒有說實話……」她低下頭,眼淚仍不斷滴落。
「妳希望我怎麼幫妳?」我問。她抬起頭,用堅定的眼神說:「老師,我無法繼續待在這個家了,請讓社會處幫我安排強制安置,」她崩潰大哭:「我不要再回家了、我不要再回家了…….」
—
我的心裡五味雜陳。每次遇到這類家暴或兒少保護事件的個案,當輔導老師的總是忙得人仰馬翻。當初我可為了妳的事,東奔西走,白忙了兩次都無功而返。這下子妳終於想通了,要我幫忙。那麼,我之前到底在幹嘛?
也或許,前兩次她都看在眼裡。她只是想知道,眼前這位號稱能夠幫上忙的輔導老師,是否是真心願意為她做點什麼;她想看看,這個人在處理事情的時候,是否足夠謹慎到讓她不再繼續受傷害。或許,對她而言,在她身旁沒有任何一個人是足以信任的了;所以,她必須一次又一次地試探。畢竟,她的處境是如此的危險。
—
當天下午,社工直接帶她去驗傷、報案,然後緊急安排了寄宿家庭。在我確認當晚她暫時可以不用回到那令她既熟悉又恐懼的家裡時,我叮嚀她:「好好照顧自己!」
她背起書包,在社工的陪同下,準備前往寄宿家庭。
我看著她走出社會處的大門,這孩子回頭看了我一眼,開口問:「老師,你真的願意相信我嗎?」
我微笑著,用力點點頭。「快去吧!」我說,同時向她揮手道別。她緊繃的神情逐漸放鬆,嘴角綻放起我從未見過的笑容。
—
我願意相信她嗎?我揣測著她為什麼要問我這句話;也認真地問我自己,我的答案是什麼?
廢話,我當然相信她,不然我在這兒做什麼?即使她矇騙了我兩次,讓我白忙一場(不!是兩場),我仍然願意相信她。
我知道,我相信她的,不是她有做什麼,沒做什麼,或者她說的是真話,還是假話。我相信她的,是不論她做了什麼,說了什麼,決定了什麼,內在都必然有著一份善意與正向的動機—這是不容質疑的。
這份相信,是一種選擇。我選擇相信人們所有行為的背後都有著正向意圖,不是想使自己更好,就是想保護自己免於傷害。
而對於一個長期處於虐待威脅家庭環境中的孩子而言,每天必須帶著恐懼生活,戰戰兢兢於不知何時會遭受一頓毒打或責罵。周遭的一切,沒有任何對象是足以令她信任的。即使她知道學校老師可以幫助她,但內心深處面對大人的不安,也讓她一再地打退堂鼓,同時一次又一次用試探的方式對自己信心喊話。
—
「妳高三了,會想繼續升學嗎?」社工問她。「會呀!而且我想念社工系,」她說:「我想幫助那些像我一樣遭遇的人。」
我知道,這孩子經歷了這次被幫助的經驗,已經發展出對人的信任了,也願意將這份信任,傳遞給社會上有需要的人。
這正是身為一位助人者,最大的成就感來源囉!
後記:
我還是覺得處理兒少保護案件這類事情實在很鳥,有繁瑣的行政流程,還得東奔西走聯繫各種資源,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。要是一個閃失,所有矛頭都會指向你,還會被個案討厭。然而,總得有人做這些事情,不是嗎?在這裡,向所有不辭辛勞的助人工作者(輔導教師、心理師、社工師、護理師…..管他什麼師的)致敬!
(本文撰寫於2015年7月18日)


_240822_7.jpg)


.jpg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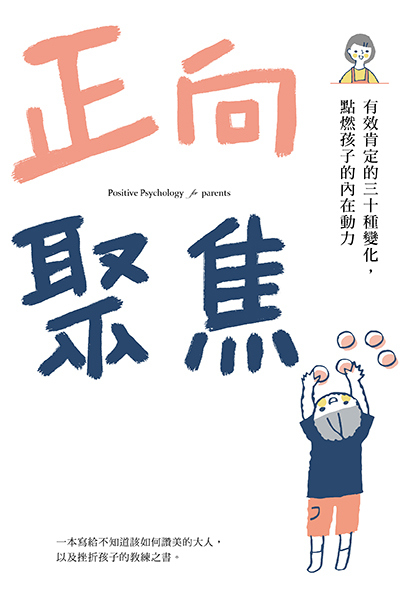
-scaled.jpg)